在纽约市晨光初现的哈德逊河畔,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玻璃幕墙映出匆匆人影,人群中,一位身着深灰运动夹克的东方青年格外沉静——他是费若秋,曾以“旅法剑客”之名震动欧洲击剑界,如今褪去战袍,成了哥大应用数学系的一名普通研究生,从巴黎赛场的金属剑道到曼哈顿的学术殿堂,这位25岁的年轻人正用手中无形的剑,pa真人视讯劈开一条迥异于传统运动员的跨界之路。
“离开赛场时,我听见了两种声音”

2022年夏季,费若秋在赢得全法击剑锦标赛银牌后突然宣布暂别赛场,转而赴美求学,消息传出,法国《队报》以“东方天才的未解抉择”为题表达惋惜,而国内体育论坛则充斥着“巅峰期留学是否值得”的争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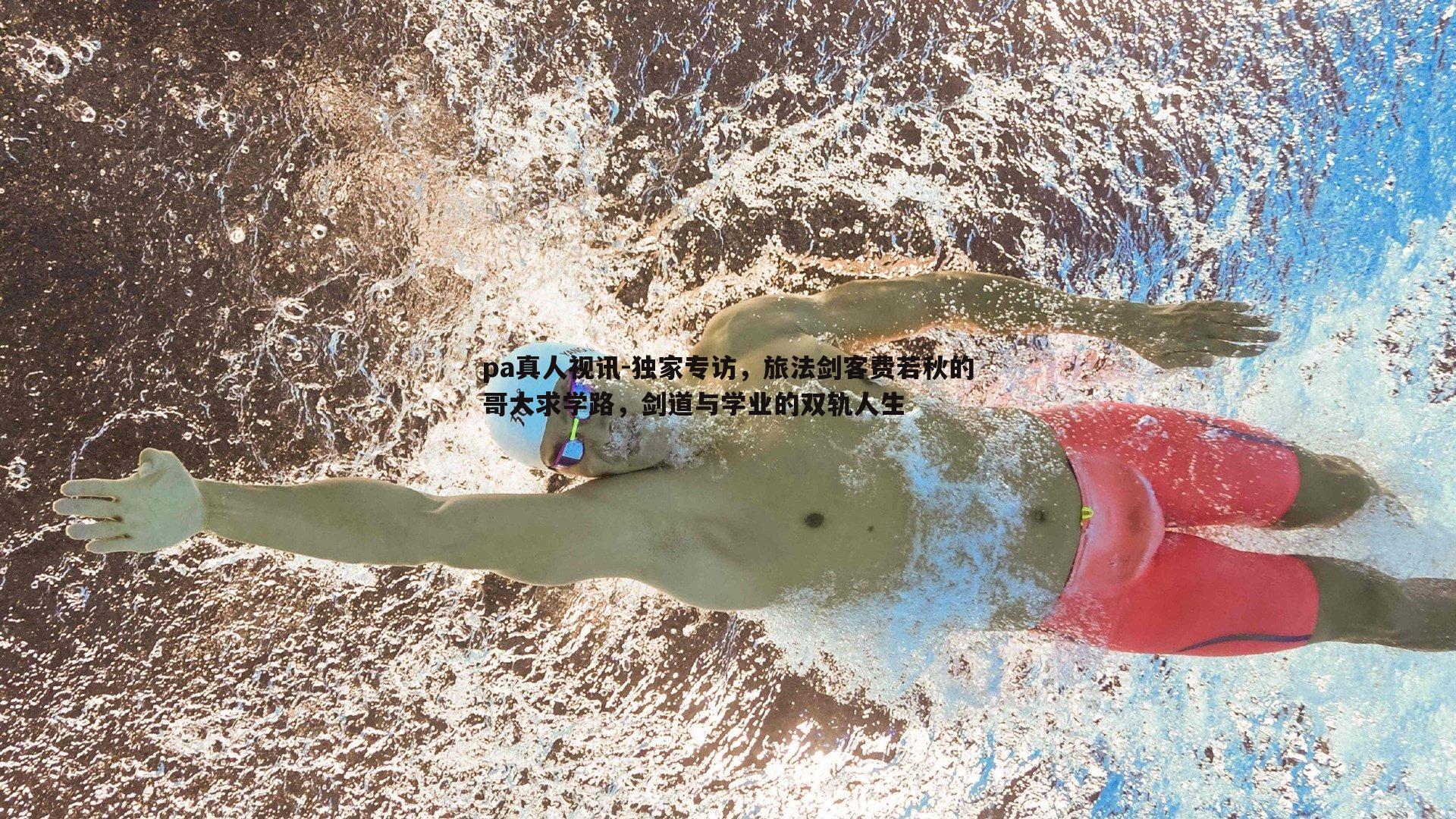
“教练说我是他见过最接近‘剑道哲学家’的选手。”费若秋转动着手中的咖啡杯,窗外是哥大著名的洛氏纪念图书馆,“但正是这种评价让我警惕——当人们开始用‘哲学家’形容运动员时,或许意味着你的技术已触及天花板。”他坦言,在法国训练的最后半年,每次取胜后的兴奋感持续缩短,“就像重复解锁同一道数学题,需要寻找新的变量”。
这种认知并非突发奇想,早在北京西城体校训练时,少年费若秋就常在训练日志里夹带微积分笔记,赴法后,他坚持每晚用两小时学习线上课程,巴黎郊外训练基地的储物柜里,总放着翻旧的英文教材。“运动员的黄金期很短,但求知的窗口期可以很长。”他说。
哥大教室里的“降维打击”
初入哥大,这位曾在赛场上冷静如冰的剑客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,应用数学系的“随机过程”课程让他首次体会到“智力上的窒息感”——那种感觉比决赛局落后四剑时更令人焦虑,为了弥补基础差距,他创造了独特的“击剑学习法”:将复杂公式写在剑袋上随身记忆,用战术分析思维拆解数学证明,甚至把论文写作比作比赛节奏控制。
“剑术讲究在电光石火间找到最优解,数学亦然。”费若秋展示着他布满剑道术语的数学笔记,泛黄的纸页上,勒贝格积分公式旁画着进攻步法示意图,这种跨界思维意外获得了系主任教授的赞赏,他的期末论文《击剑决策树与博弈论建模》被选为课程范本。
但平衡学业与训练需要近乎严酷的自律,每天清晨五点半,当同学们还在沉睡,费若秋已经出现在哥大体育馆进行核心训练;午休时间则在图书馆地下室进行无人观看的剑术练习;晚上十点后,才是他雷打不动的学术研究时段。“这种节奏比职业运动员时期更辛苦,但精神上更自由。”他说。
“第三文化”的融合智慧
作为同时经历中式基础训练、欧陆职业淬炼和美式学术熏陶的“第三文化”运动员,费若秋对三种体育生态有着独特观察。“法国教练强调‘剑如其人’,中国教练重视‘基本功堆砌’,而美国体育文化最让我惊讶的是数据驱动。”他正在参与的运动科学实验室项目,正是利用机器学习分析击剑运动员的生物力学数据。
这种跨界视角也让他对体育本质产生新理解,在最近提交的课程论文中,他写道:“现代击剑的危机不在于观众流失,而在于过度专业化导致的思想贫瘠,当运动员不再阅读文学、不再思考数学、不再关心赛场外的世界,这项起源于文艺复兴的智慧运动正在变成机械的肌肉记忆。”
在剑尖与笔尖之间
尽管课业繁重,费若秋并未真正远离剑道,他每周会指导哥大击剑俱乐部的学生,偶尔飞往欧洲参加表演赛,更重要的计划是开发结合运动科学与人工智能的训练系统——“就像阿尔法狗颠覆围棋,击剑同样需要技术革命”。
问及是否考虑重返职业赛场,他给出一个典型的数学系答案:“这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,就像击剑中的复合攻击,看似指向一个目标,实则涵盖多个维度。”他透露正在申请运动生物力学方向的博士项目,希望打造连接竞技体育与学术研究的桥梁。
夕阳透过办公室的百叶窗,在墙面投下明暗相间的条纹,恍若剑道馆的标记线,费若秋收拾好背包,准备赶往晚上的实验室会议。“有人问我从冠军到学生是否算一种退步。”他站在门口微笑,眼神仍如剑道上那般锐利,“但真正的进步,是拥有选择赛道的自由,现在我的赛场变大了——从十米剑道到整个人类知识前沿。”
这个曾经用剑锋定义自我的年轻人,如今在哥大的古老回廊里,正以更从容的姿态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命题:当一名运动员同时成为思考者,他挥出的每一剑都在拓展运动的边界,而在剑尖与笔尖之间,费若秋找到了比任何奖牌都更恒久的立足之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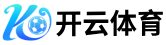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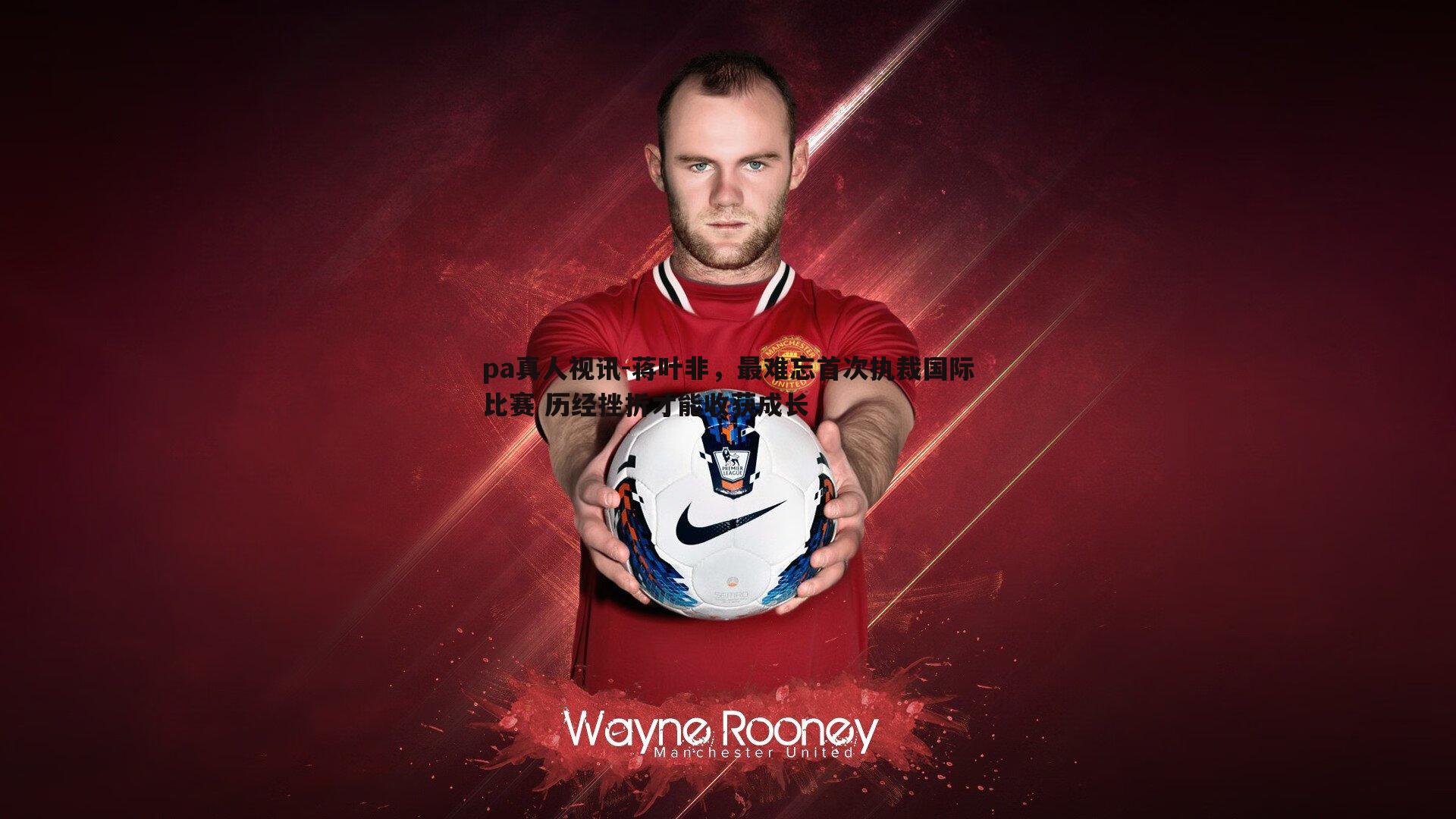



发表评论